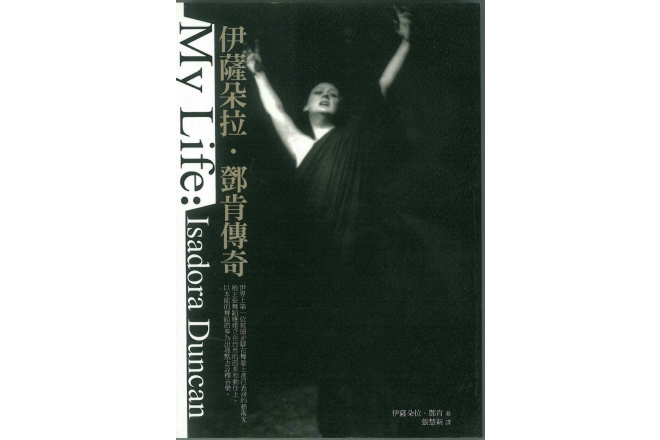
伊藤朵拉·鄧肯傳奇
說實話,當別人一開始建議我寫這本書時,我還有些忐忑不安,這倒不是因為我的生活經歷不像小說那樣豐富有趣,或者不像電影那樣精彩刺激,也不是因為我擔心這本書寫成以後,無法成為一本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傳記,我擔心的只是如何把它寫出來──對我而言,這確實是一個問題。
為了一個簡單的舞蹈動作,我經常要花上幾年的時間去研究和探索。我也很瞭解寫作這門藝術,我知道,要想寫出一句既簡單又精彩的話,同樣也需要我花費多年的心血。我始終有這樣一種看法:有的人可以不遠萬里,到赤道地區降獅伏虎,幹出一番轟轟烈烈、驚世駭俗的事業,但如果讓他把自己的事蹟形諸筆墨,他可能也會變得左支右絀;有的人雖然足不出戶,卻可以把在叢林中降獅伏虎的經過,描繪得活靈活現,使讀者有身臨其境的感覺,甚至能夠感覺到作者的劇痛與驚恐,能夠嗅到獅子的氣味,能夠聽到響尾蛇所發出的可怕的啪啪聲。想像力是最為重要的。我沒有塞萬提斯的生花妙筆,甚至比不上卡薩諾瓦,我那曲折豐富的生活經歷,恐怕會在我的筆下失去其應有的韻味。
還有一個問題就是,如何用文字來再現真實的自我呢?我們真的瞭解自己嗎?朋友們對我們有一種看法,我們自己對自己也有一種看法;愛我們的人對我們有一種看法,仇恨我們的人對我們也有一種看法,所有這些看法都是不一樣的。這些話並非無稽之談。就在今天早上喝咖啡時,我看到了一份報紙上的評論,作者說我是美麗絕倫的天才;就在我臉上的笑容還未褪去時,我又隨手拿起了另外一份報紙,上面的文字居然把我說成了一個醜陋不堪的庸才。我決定以後再也不看有關我的評論文章了,我不能阻止別人去評論我,讚美的話固然會讓我心情愉快,但批評指責的話,也著實讓我心灰意冷,而且這些話往往還帶著惡意的人身攻擊。
柏林有一位批評家對我總是挑三揀四,甚至說我根本就不懂音樂。為了讓他明白自己的錯誤,有一天我寫信邀請他當面談談。他來了以後,我們相對而坐,我努力地向他講述我根據音樂創造舞蹈動作的理論,足足講了一個半小時,可是我卻發現他遲鈍、愚蠢至極。最令我啼笑皆非的是,他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副助聽器,告訴我他耳朵很背,即使戴上助聽器、坐在第一排,也很難聽清楚樂隊的演奏。讓我夜不能寐的評論,竟然就出自這樣一個人之手!
既然別人對我們的看法是如此的千差萬別,我們又如何能在本書中,寫出更新的人物形象呢?是該寫成是聖母瑪利亞,還是淫蕩的瑪薩琳娜?是從良的妓女瑪達琳,還是才華橫溢的女人呢?在她們的經歷中,我如何能夠找到女性的形象?當然,真實的女性形象也許不只一個,而是成百上千,但是我的靈魂超乎尋常,從來不受她們之中任何一個人的影響。
有人說的好,做好寫作的基本前提,就是作者對自己所寫的內容從來都沒有經歷過。當你想將自己的親身經歷用語言表達出來時,你就會感覺到這些語言是有多麼的難以捉摸!對往昔的記憶並不像夢境那樣生動有趣。我做過的很多夢,都要比真實經歷的回憶要生動有趣得多。幸好,人生如夢,要不然又有誰能夠承受得了一生中如此之多的經歷呢?
比如那些經歷過「露西塔尼亞號」豪華輪沉沒事件的倖存者們,也許人們會覺得他們臉上會銘刻著永恆的驚恐,但事實並非如此,不論在哪兒遇到他們,我都能從他們臉上發現幸福快樂的笑容。只有在浪漫的故事裡,才會發生身心突變的事情。而在現實生活中,即便歷經大喜大悲、大驚大恐,人們仍會依然故我。你看那些俄國的逃亡貴族,他們在失去了曾經佔有的一切之後,現在還不是像戰前一樣,夜夜在蒙馬特大街上與歌女們醉生夢死嗎?
不管什麼人,只要能夠如實地寫下自己的生活經歷,都能使之成為一部傑作。但是沒有幾個人敢於寫出自己生活的本來面目。讓.雅克.盧梭為人類作出了最大的犧牲,他如實地袒露了自己的靈魂、最隱秘的行為和內心深處的思想,因此他寫出了一部不朽之作。沃爾特.惠特曼向美國人民展現出了最真實的自我,他的作品曾一度以「不道德的書」的名義被查禁。現在看來,這項罪名真是太荒唐了。不過直到今天,還沒有哪一位女性能夠如實地講述自己生活的全部。許多著名女士的自傳,講的只是自己生活的表像,以及各種瑣事和趣聞,全都沒有觸及到自己真實的情感和生活。每當行文到歡樂或痛苦的關鍵時刻,她們便都奇怪地顧左右而言他了。
我的藝術就是透過舞蹈的動作和節奏,來努力地向世人展現真實的自我。因此,為了發現一個絕對真實的動作,我往往需要花費幾年的時間。這與用文字來表達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。在蜂擁而至的觀眾面前,我可以隨心所欲地用舞蹈藝術,來展示我心靈深處最隱秘的衝動。從一開始,我的舞蹈就是用來展現自我的。在童年時代,我用跳舞的方式,來表達自己對於萬物生長所感到的那種難以抑制的歡樂。少年時期,當我初次意識到生活中存在悲劇的一面時,我的舞蹈便開始由歡樂轉向憂鬱,我為生活的殘酷和時間的流逝感到憂鬱。
十六歲那年,有一次我在沒有音樂伴奏的情況下表演舞蹈。舞蹈結束時,有一位觀眾突然喊道:「這是死神與少女」於是這段舞蹈就起名為《死神與少女》。這不是我的本意,我最初只是想表達自己對一切歡樂表像下隱含的悲劇的認識,因此,按照我的本意,那段舞蹈應該叫《生命與少女》的。後來,我便用舞蹈來表現自己對於生活的抗爭,表現生活中難得一見的瞬間歡樂。沒有什麼人能夠比電影或小說中的主角更為脫離現實的了。這些人往往具有出眾的美貌和高尚的品德,絕對不會犯什麼錯誤。男主角一定是高貴、勇敢,女主角肯定是純潔、溫柔。所有的卑鄙和罪惡都出現在「壞男人」和「壞女人」的身上。
其實,我們知道,生活中的人是不能簡單地按照好、壞的標準來劃分的。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觸犯「十戒」,但他們肯定都有觸犯的能力。我們每個人的身上,都隱藏著另一個不守清規戒律的自我,一有機會,「他」就會跳出來。一個人之所以品德高尚,是因為他還沒有受到足夠的誘惑,或者是他的生活較為單調平靜,或者是他專心致志於某事而無暇他顧。
我曾經看過一部叫《鐵路》的電影,大概內容是說人的一生,就像在固定軌道上運行的火車一樣,一旦火車脫軌或遇上難以逾越的障礙,災難就會降臨。幸運的是,當司機看到陡峭的下坡時,沒有產生惡魔般的衝動,要不然,他就會關閉所有的制動裝置,而使火車衝向無底的深淵了。
曾經有人問我愛情是否高於藝術,我說兩者是不可分割的,因為藝術家都是真正的性情中人,他們對美有著一種至純至真的理解。當他滿懷愛心去對待永恆的藝術之美時,藝術就成了對心靈的闡釋。
在我們這個時代,最了不起的名人,也許應該算是加布里埃爾.鄧南遮【注:加布里埃爾.鄧南遮(1863—1938),義大利詩人、小說家。他對美有著敏銳的感覺和豐富的表現手段,善於精確地捕捉和展示自然界的美和色彩。他的作品文字優雅、柔美,對義大利現代文學和語言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主要作品有詩集《新歌》和小說《死的勝利》等】了。儘管他的身材不高,而且只有在笑起來時才算好看,但是當他與他所愛之人交談時,卻能變得像阿波羅一樣富有魅力。加布里埃爾.鄧南遮贏得了當今世上最著名、最美的幾位女人的愛。當鄧南遮愛一個女人時,他能夠讓她情緒高漲,使她覺得自己彷彿一下子從肉體凡胎,變成了仙界的貝雅特里奇。但丁也曾經為貝雅特里奇寫下許多不朽的讚歌。有一個時期,巴黎曾一度對鄧南遮崇拜成風,幾乎所有的美女都愛上了他。受到他寵愛的女人,彷彿都蒙上了一層閃閃發光的面紗,在言談舉止間,她們的臉上都洋溢著不同凡響的神采。但是當詩人的熱情褪去之後,面紗也隨之消失,這些女人神采不再,便又恢復到了肉體凡胎的樣子。她自己也許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,但卻能感受到這種從神仙到凡人的突變。
回顧以往受鄧南遮寵愛的日子,她會覺得鄧南遮是這個世上可遇不可求的情人,於是也會更加哀歎自己的命運,心情會變得更加悲涼,也許有一天人們遇到她時會不解地說:「哎呀,鄧南遮怎麼可能喜歡這個姿色平平的紅眼睛女人呢?」鄧南遮的愛的力量就是如此的偉大,它可以讓最平淡無奇的女人,擁有天仙般的容貌。
在鄧南遮的一生中,只有一個女人經受了他這種魔力的考驗。這個女人原本就是仙女貝雅特里奇的化身,因此也就無需鄧南遮向她投去面紗了。我一直覺得埃莉諾拉.杜絲【埃莉諾拉.杜絲(1858—1924),義大利女演員。她善於對人物內心世界進行樸實無華、細膩委婉的剖示,因此形成了鮮明的表演風格。她戲路廣闊,既擅長悲劇,也擅演喜劇。她在戲劇舞臺上成功地塑造了茱麗葉、奧菲利婭、娜拉等女性形象,受到歐洲許多國家的熱烈歡迎。】就是但丁筆下的貝雅特里奇的化身。鄧南遮對她只能是仰慕、傾倒-—這的確是他快樂的一生中絕無僅有的事情。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別的女人,唯有埃莉諾拉像神靈一樣高高在上。
面對美妙的讚譽,人們是多麼無知啊!鄧南遮的讚譽,就像夏娃在伊甸園中,所聽到的毒蛇那不可抗拒的誘惑一樣,具有非凡的魔力,能夠讓任何女人都覺得自己是世人關注的焦點。
我曾經與他一起在林中漫步,當我們停下來時,誰都沒有說話,然後鄧南遮突然感歎道:「啊,伊薩多拉,只有與你獨處的時候,才能領略大自然的美妙。別的女人會把風景都糟蹋了,而你卻能與大自然融為一體,你和花草、藍天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,你就是主宰自然的女神。」試問有哪位女子能夠受得了這樣的贊詞?
這就是鄧南遮的天才,他能夠讓每個女人都覺得自己是一位女神。
躺在內格拉斯的床上,我努力地回憶過往之事。我感覺到了米迪那炎熱的陽光。我聽到了附近公園裡孩子們嬉鬧的聲音。我覺得自己全身都變得暖融融的。我看到我赤裸的雙腿隨意地舒展開來,柔軟的乳房與雙臂從來都沒有靜止過,它們總是輕柔地波動著。我意識到,十二年來我始終疲憊不堪,我的乳房一直在隱隱作痛。我的雙手充滿了憂傷。當我獨處時,我的雙眼很少是乾著的,我的淚水已經流淌了十二年。十二年前的一天,我在另一張床上睡覺,卻突然被一聲大喊驚醒,我看到洛【指英國百萬富翁洛亨格林,他當時正與鄧肯同居】像一個病人一樣,對我說道:「孩子們都死了。」
我記得當時我似乎像突然得了一種奇怪的病一樣,覺得喉嚨灼痛,就像吞下了燒紅的煤塊。但我不明白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我想安慰他,溫柔地對他說,這不是真的。後來又進來一些人,我更加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接著,又進來了一位留著黑鬍子的人,有人對我說他是醫生。醫生說:「這不是真的,我要救活他們。」
我相信了他的話,並想跟著他一塊進去,但是人們攔住了我。我現在才明白,他們是不想讓我知道孩子們確實是不行了。他們怕我承受不了這樣的打擊。可我當時的心情卻很高興。看見周圍的人都在哭,我倒是很想去安慰每一個人。現在想想,還是搞不清為什麼當時會產生這種奇怪的心情。我真的看破紅塵了嗎?我真的知道死亡是不存在的嗎?難道那兩個冰冷的小蠟像並非我的孩子,而只是他們脫掉的外套嗎?我的孩子們的靈魂會不會在天堂中得到永生?
在人的一生中,母親的哭聲只有兩次是聽不到的-—一次是在出生前,一次是在死亡後。當我握住他們冰涼的小手時,他們卻再也無法握住我的手了,我哭了,這哭聲與生他們時的哭聲一模一樣。一種極度喜悅時的哭聲,一種極度悲傷時的哭聲,為什麼會是一樣的呢?我不知道是為什麼,但我知道這哭聲真的是一樣的。茫茫人世間,是不是只有一種偉大的哭聲-—一種能夠孕育生命的母親的哭聲,既能包含憂傷、悲痛,又能包含歡樂、狂喜呢?